原标题:文苑热土|国色芳华我自爱


我家的牡丹,活了40年,与我年龄相当。
我一岁时,母亲在平房上垒土种下了它,从此,它便与我一同在岁月里成长,头顶同样的蓝天,呼吸一样的空气,喝着同一水管流出的水,说它和我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真是再恰当不过。我亦偏爱这样美好的说法,仿佛我们之间,自始至终,都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羁绊。
那时我尚小,牡丹也同样稚嫩。平房上的泥土,是母亲一背篼一背篼背上去的,垒起了厚厚一层,足有40厘米,只为给牡丹营造一个家。小小的牡丹,被安置在土块的正中央,宛如母亲的第二个孩子,养在深闺中,连我这个嫡系的孩子都难以得见。母亲看得紧,不准我爬高踩低,尤其严禁我上平房顶。我与牡丹,就这样被隔离开来,虽同在一块天地,却难以相见。
我不知道牡丹生长的快慢,我看不到它,它也看不到我。房顶上的牡丹,成了我心中的执念。
我每天都朝着房顶上看,满心期待有一天能看到什么,可日复一日,什么也没看到。即便如此,我依然每天都看,仿佛这样便能与牡丹建立起某种联系。就如泰戈尔所说:“眼睛为她下着雨,心却为她打着伞 ,这就是爱情。”我对牡丹的这份期待,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情感呢?
我看见母亲每天都上楼浇水,硬生生把一面火砖墙,浇成了一幅油画,墨绿的苔藓,土黄的火砖,一大片黄中带着墨绿,色彩中庸,别具一番美感。木梯靠在一面墙上,墙承载了楼梯的重量,也承载了母亲的重量,还有背篼里石头的重量。母亲上上下下无数回,背了多少土,多少石头,我并不清楚。或许那面墙是清楚的,它见证了母亲的辛勤付出,也知道这些石头和土块压在母亲肩上的重量。
石头被母亲一个个、一排排罗列,像垒墙一样垒起,不用担心下雨或积水时被冲塌。这些土,这些石头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只为了一株小小的牡丹,牡丹该是何等的荣耀。
人,总是被好奇心怂恿着,无限地好奇。我趴在木梯上,想要上去看看,爬上几梯后,却不敢下来了。我的腿颤抖着,木梯也颤抖着,我感觉木梯腿不一样长,担心它会朝着腿长的一边倾斜,朝腿短的一边倒下去。慌乱中,我看见木梯的一端离开了墙面,翘了起来。我挂在木梯上,地面在我眼前倾斜了。我被母亲接下了楼梯,在惊慌中看着母亲撤走木梯,将它置于离平房远远的地方。许久,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不能挪动。
我恨自己不能快一点长大。我与牡丹之间,隔着一部木梯的距离,这距离,那么近,却又那么远。让我对牡丹的渴望愈发强烈。“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而我对牡丹的这份期待,便是我在那段时光里的“起舞”。
母亲说,等花开,等长大,就可以上去了。
我等了又等,盼了又盼,不知道什么时候花会开,什么时候自己就长大了。不过还好,有了盼头,日子过起来就没那么漫长了。
我小学快要毕业了,花仍然没开。母亲到处打听、询问,如何才能让它开花。这时的牡丹,长得极好,像一个穿着绿色短裙的小女孩,青涩、纯洁,带着幽幽的清香。
长久地仰望,成了我的习惯。终于,我看见平房上,一片绿裳在微风中摇曳,我闻到了淡淡的清香,离我那么近,那么近,一直萦绕在我的鼻尖周围。
不知道母亲在哪里听来的,说牡丹要配上芍药才会开花,便四处找寻芍药。找回的芍药怯生生的,它仿若哪家多余的孩子,被倒插门进了我家。它偎依在牡丹的身旁,唯唯诺诺,小心翼翼。
或许有了芍药,牡丹不再孤单。我想,牡丹应该会开花了吧。
初中二年级的端午,我回到家中,看见碗口大的几朵牡丹,迎风怒绽,雍容华贵地探出了头,点缀着布满青苔的那面墙,浓艳、明亮。我踮着脚尖、伸长脖颈张望,看见一大片的花全开了。我张望的滑稽形象,仿佛把一片花全惹笑了,它们笑着笑着,全都羞红了脸,白中透着粉,粉中透着白。瞬间,荷尔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夹杂着幽幽的香味,那香味是什么,我说不清。那种粉白的色彩,又白又嫩的色彩,是我目光中渴望和积攒多年的色彩。我虽然不能像蜜蜂一样围着它转,但可以静静观看,也是一种莫大的满足。
门前,赶端午场,热闹极了,街道上摆满了蒲公英、大丽、紫藤、牡丹、菖蒲,像一个大花园一样。这些风姿别具的花,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坚强、勇敢;美好、幸福;团圆、情谊;富贵、吉祥。
我独爱牡丹,独爱其富贵华美。它如此尊崇,从小就在我仰望的目光中,和我一同成长。虽然在我面前如此低调,没有任何高姿态,却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我不再害怕,我已经长大,我挪动了楼梯,爬上了楼顶,近距离地待在牡丹的身旁,品它盛开的姿态,看它娇羞的面容。母亲在楼下大声喊着,摘几朵花来。我明明听得很清楚,伸手的瞬间又缩了回来。我实在有些不忍心,多好的花呀。
下楼见到母亲,母亲见我两手空空,问花呢。我回答,还是别摘了。母亲说,这是食用牡丹,不吃,坏了可惜了,还说要给我做碗牡丹鸡蛋汤。想着,可以将牡丹融入我的胃里,让它和我的身体重叠,我是十万个愿意的。
我再次爬上了楼顶,摘下最大最艳的两朵,去除花蕊和花蒂。母亲将花瓣洗净,放入已经煮好的糖水鸡蛋里,水再次翻涨后,母亲熄了火,给我盛了一碗牡丹鸡蛋汤。汤水裹挟着花瓣沿着我的食道层层递进,我感觉它到了我的胃里,温暖、甜蜜地盛开着。我突然想着口吐芬芳这个成语,牡丹如此高贵,食用它的人应是典雅之人,理应口吐芬芳,方能不负此国色天香。
2002年,我家建新房,平房要拆除了,牡丹花要移栽。为了让它活下来,我们选择了五月的某天,顶层封顶后的几天,开始移栽。我和母亲,还有两位亲戚,一起移栽牡丹。我先用铁锨将周围的土块铲除一些,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生怕伤了它的根本。然后每人各持工具,去掉大的土块,我用铲子在根的周围取土,母亲看我慢悠悠的,有些着急了,可她哪里知道我的想法。
我看见土块下的蚯蚓翻卷着身体,痛苦万分,反应强烈。蜗牛缓慢地伸动着触角、鼻涕虫黏糊糊地耷着,他们不知道大祸临头,还用一贯的态度坦然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其余藏匿土中的小虫纷拥乱窜,一时间场面紧张。搬迁工作扰乱了它们的世界,增加了它们死亡的概率,那又能怎么样呢,从我们要保牡丹的那刻起,其余的东西都成了弃子。它们注定在我们布下的局中慢慢消失、死去,或者和泥土混融,变成了泥土。
牡丹的根,在我们辛勤的劳作中慢慢完全呈现出来。这是一棵老根,枝枝杈杈,盘根错节,像置于血脉深处的血管,某些部位静脉曲张,隆起了一小块,一小块。
我们四人合力,将去土的牡丹抬出,走一段,又放下歇一段,沿途又落下了不少泥土和牡丹的根。牡丹“大型手术”后不能动弹,死沉死沉的,我分明看见它在颤抖,多么柔弱,多么需要呵护呀!我想,绝不能让它死去,更不能死在它的前头。那样就没有人照顾它了。
终于移到了目的地,要开始填土了,我们将原来的土背来当填土,那是牡丹熟悉的味道,不会那么生分,也不会排斥。我在原来的土里用铁锨翻找着,去除垃圾杂物,以作备用。我找到了它留下的很多根,脱离了它的身体留在了这里,我小心地捡拾着,捡起一截,放在鼻边嗅嗅,说不出的味道,不是清香,而是另一种味道,像是人身上某个部位的味道。
我看见泥土周围不远处有只鼻涕虫。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不管是鼻涕虫还是蜗牛,都想纠缠牡丹呀。牡丹见着它们,似好女怕朽夫一样的心情。我对牡丹是缺少关心的,我这么多年都不清楚它过得到底怎么样,牡丹或许不在意这些,给它浇浇水它就满足了吧。多么乖巧又多么容易满足呀。看着那讨厌的鼻涕虫,我有点心疼牡丹了,我想,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待它,哪怕是替它捉捉讨厌的鼻涕虫也好。
2003年端午,我带着爱人回家,她是一名画师,走哪里都背着颜料、画板,这次也不例外。牡丹花开,也不例外。我带她看牡丹,也让牡丹看看她,她们多像呀,一样的娇艳,一样的需要保护。她一朵一朵地看牡丹,手指在鼻尖上蹭了蹭,说,我为你画牡丹吧,画两朵,一雌一雄,可好。我大喜,我不知道牡丹花如何分雌雄,也不知道雌雄的牡丹放在一起如何辨雌雄。
画纸徐徐展开,我看见她笔蘸白粉,笔尖蘸玫红,用皴行的方法画花瓣,涂花瓣,描芯包,逐步向外扩展。手法娴熟,晕染得当,我不禁有些许陶醉,仿佛看见她在给自己化妆,就像胭脂在脸上晕开一样,白中透着粉,粉中透着白。雌雄的辨认也大有来头,原来是用花蕊来分雌雄的。我大长见识,雌蕊中心形如石榴,雄蕊四周排列整齐,中藤黄加白粉勾线填色……我确确实实看见了两朵花,雌雄并蒂,娇艳地盛开在她的纤纤玉指下。从此,我的梦里梦外多了一幅画,一幅关于牡丹,关于爱情,关于我和她的画。
这次画画,实实在在地说,我眼里只看着她认真画画的模样,真正的牡丹在我眼前晃过,居然第一次被我忽略了。我不知道我竟是如此的人,但又不能说我不喜牡丹了,我无法解释梦里梦外的牡丹。
后来我到过“牡丹之都”菏泽,欣赏过那里红得似火、白得似雪,绿得似玉,黄的、粉的,各有千秋的牡丹,美得让人惊叹,令人窒息。我又想起了家中的牡丹,形单影只,孤零零地在暗夜里,它成了暗夜的一部分,在我眼前摇曳。
那日,牡丹又出现在我梦里,没精打采、蔫巴巴的,像害了大病一样。醒来后,我有些忐忑。
我加速了回家的行程,我想第一时间看看牡丹。牡丹确实病了,花叶萎靡、蜷缩。我看见无数的白色小虫,密密匝匝布满了花茎和花叶,让它呼吸困难。我呼吸也困难、急促,我忽略了对它的呵护,让它遭此大劫。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活过来。我给它施肥、浇水、喷药,在离它两三尺远的地方,浅浅地撒上了石灰粉。我想,蜗牛、鼻涕虫,不敢靠近它了吧,如果它们要强行越线闯关,那么石灰线便是它们的炼狱。
做完这一切后,我终于可以休息了,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放松,我要等待的是,牡丹重新绿起来。
夜里,我梦见牡丹花周围好多的鼻涕虫和蜗牛,它们蠕动着身体向牡丹靠近,牡丹颤抖着,我也在梦里颤抖着,突然一只刺猬窜了出来,鼻涕虫和蜗牛,成了它的食物。
生命的轮回与希望,或许就在这不经意间展现。正如尼采所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我期待着牡丹在经历这场磨难后,能更加茁壮地成长,继续在岁月里与我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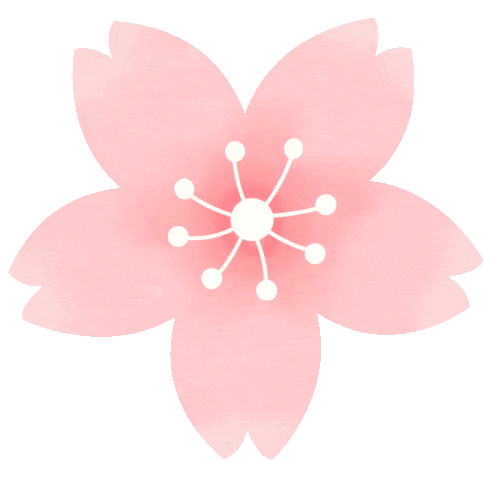
END
作
者
简
介
刘仕川,主任编辑,昭通市融媒体中心创意设计部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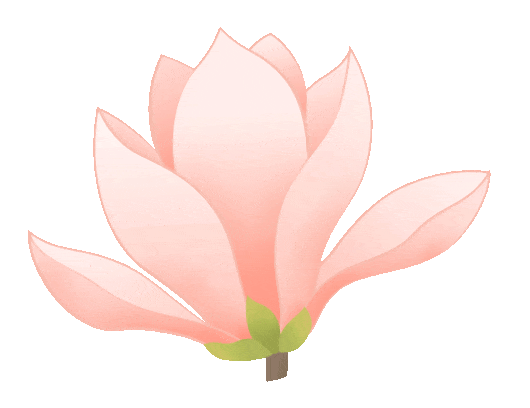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
3822183642@qq.com
文章仅用于“云南政协报”微信公众号,无稿费。
编辑:何健美
二审:欧阳文军
终审:张居正
 (云南政协报)
(云南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