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苑热土|稻花香里说丰年

我走在田埂上,稻穗在风里轻轻摇曳,鼻尖漫入熟悉的香。这香裹着阳光的暖、泥土的芬芳;这香牵着记忆往回走,走过八十年代的煤油灯,走过九十年代的板车辙,一直走到母亲如今弯腰抚摸稻穗的身影里。四十载风风雨雨,稻浪涨了又落,可这香气总在这儿,引着我想起:每一缕香里,都藏着对丰年的盼。
01
我对世事的记忆,是从八十年代初的稻花香里开始的。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拂过乡村,包产到户的政策让田埂上多了几分忙碌,可我家的饭桌上,总摆着掺了苞谷面的饭,一年里总有个把月,米缸是见了底的。
饿肚子的夜晚,昏黄的煤油灯把父母的影子拉得很长。他们总在饭桌旁盘点收成,声音里带着无奈:没钱买化肥,地里的草比稻子还疯长;稻瘟病一来,半田的稻穗就枯了;蝗虫飞过,叶片上尽是筛子眼;连麻雀都敢成群结队来啄刚灌浆的稻穗;旱季,田裂得能塞进拳头;雨季一来,又眼睁睁看着稻穗泡在水里发霉;刚分了田地,还不懂种田技术。父亲卷着旱烟,烟圈里裹着叹息:“种一坡,收一锅,不是瞎忙嘛!”
可叹息完了,他们在油灯下谋划:要把西边那片坡地改成水田,增加种植面积;“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要在牛圈旁垒个大粪池,把猪粪、牛粪都攒起来;要去信用社贷款,买新粮种、化肥、农药,再买本种稻子的书。
秋种刚结束,父亲就带着工具去了西坡的自留地,蹲在地里用水平尺量了又量,用石灰勾画出田埂的轮廓;母亲和姐姐们便挥着锄头挖土,用撮箕一趟趟把土运到田埂上。秋阳把她们的脊背晒得黝黑,汗珠砸在干裂的土地上。一个月后,两亩多的水田真的成了形,田埂整整齐齐,父亲又疏通了周围的沟渠,脸上笑露出两排被日久烟熏过的牙。
从那时起,每天放学回家,我和姐妹们一放下书包,就提起小撮箕出门。眼睛像探照灯似的扫过路面,瞧见一堆猪粪或牛粪,就赶紧用小铁铲小心翼翼地收进撮箕。有时粪堆冻在地上,得用铲子一点点撬;遇上稀牛粪,溅得满手都是,也顾不上擦,只想着赶紧送到家后的粪池里。那粪池像个聚宝盆,积攒着我们对来年丰收的渴盼。
开春时,父亲真的从信用社贷了款。他揣着钱去了县城,带回尿素、农药;带回一包沉甸甸的稻种,袋面上印着“楚粳”;还带回了《水稻栽培技术》,这书成了他的宝贝,晚上在油灯下翻得卷了边,空白处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分蘖期施氮肥”“扬花期防螟虫”。
栽秧时,父亲把攒了一年的粪肥均匀地撒进田里,犁田时埋进泥里,黑黝黝的泥土泛着油光。秧苗栽下去没多久,就噌噌地长,分蘖得密密麻麻。到了扬花期,父亲背着喷雾器打农药,又追了次肥,稻穗沉甸甸地弯下腰,风一吹,稻浪里滚着香。灌浆时,我们姐弟轮着去田里赶麻雀,站在齐腰的稻丛里,谷香钻进鼻孔,馋得直咽口水。
收割时节,田埂上都是欢笑声。姐姐们挥着镰刀割稻子,稻茬齐整整的;我和妹妹抱着稻捆,往打谷机旁送;母亲蹬着打谷机,踏板吱呀作响,金黄的谷粒簌簌落在帆布上;父亲背着鼓鼓的谷包往家走,脊梁弯得像张弓,脚步却稳当。
交完公余粮,楼上堆着满仓谷,院子里晒的谷子金灿灿的,连空气里都飘着米香。碾米机转起来时,白花花的米粒流进米仓,母亲首先舀起一碗新米饭递给我,阳光透过米粒,亮得晃眼,冒着热气。我扒了一大口,香得直咂嘴。父母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比蜜还甜的笑意。
后来每年秋天,我家的稻田都金灿灿的。父亲总说:“好日子不是等来的,是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风掠过稻穗的声音里,藏着我们一家人的汗水,也藏着那个年代里,最踏实的希望。
02
我望着熟悉的稻田,稻穗在风中低吟,像又在复述那些浸着汗水的丰年岁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二姐去昆明读大学那年,三姐正在临沧读卫校,我背着帆布包去楚雄民族师范学校报到,小妹背着褪色的书包走进初中的校门。家里的开销一下子大了起来。父母亲为挣钱供我们姐弟读书,操碎了心。除了学栽烤烟,农闲时打短工,养母猪卖仔外,没什么文化的父母只能操起老本行,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盼望水稻丰收,多卖粮食,换取钞票,保证我们姐弟在校的吃穿用度。
父亲经过和村里田多人少的家庭协商,承诺付给租金,租到了十余亩稻田,加上我家原有的,计划栽种十七亩水稻。
元宵节刚过不久,母亲就开始烧草灰,她总念叨:“草木灰能壮苗”;筛牛粪时,指缝里的泥垢要到插秧结束才肯褪净。父亲整理秧田,泡稻种、撒稻种,管理得无微不至,水深了就撤水,水少了就添水。
栽秧时节的月光格外凉。父亲常常夜间引水泡田,白天驱牛犁田;母亲常常夜间拔秧,白天插秧。父母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劳作了近一个多月,十七亩稻田才换上整齐的绿装。
秋收的日子,镰刀总比星星醒得早。母亲夜间摸黑一刀一刀割谷子,白天蹬打谷机;父亲头顶烈日,脚踏黄土,将金黄的稻谷一大袋一大袋背回家。每当看到父亲和母亲才过四十,就身材佝偻、肤色黝黑、满脸皱纹、华发早生、未老先衰,我常暗自流泪。
稻谷分批晒干扬净,交完公余粮,留够口粮,剩下的便要变成我们的读书费用。父亲借来板车,和母亲把稻谷运到加工房碾成米,每五十公斤装成一袋。清晨六点的小路溪街,露水在板车轱辘上结霜,母亲裹着旧围巾坐在米袋上,头发里缠着草屑。换来的钞票用手绢裹着,角角都磨得发亮,父亲舍不得买他爱吃的猪下水,母亲舍不得添件新衣裳。就这样一分一分攒着,一角一角存着,待每学期开学时,又一打一打地分给我们姐弟拿去读书。
师范二年级暑假,看到父母又比上次见到时衰老了很多,我心痛不已。“别这么苦了,去信用社贷点款吧。”我声音发颤地劝父亲,“等我们工作了就还。”他磕了磕烟灰:“只要没有天灾人祸,一直像这几年一样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我和你妈不会让你们背债。”烟圈飘到稻穗上,那些饱满的颗粒仿佛也在点头。丰收成了我们全家的期盼。
后来几年,老天爷格外眷顾。金黄的稻浪一年年漫过田埂,把父母的辛劳酿成我们书包里的课本、身上的新衣、碗里可口的饭菜。师范毕业回到老家那天,我在田埂上,看见父亲正弯腰捆风倒的稻穗,阳光在他花白的发间跳跃。这三年里,他没向人借过一分钱,没往信用社跑过一次。
如今走在田埂上,闻着稻香,总让我想起父母在稻田里的身影。那些稻穗里藏着的,不只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双双不肯弯下的脊梁,在岁月里撑起了我们姐弟的前程。
03
我们姐弟工作后,日子越过越宽裕。姐妹们总记挂着父母,每年给他们添置衣物,给父母大把的零花钱;家里的粮仓总堆得满满当当,后院里鸡鸭成群;我在老家给父母盖了栋小楼,又申请回村任教,守在父母身边,他们有个头疼脑热,我总能第一时间照应。可父母,终究舍不下那些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
坡地上的玉米是父母的牵挂。每年五一节,我带着妻儿随父母下地,我和父亲抡着锄头打塘,母亲点种,妻子、儿子盖土,田埂上的野花开得正艳,一家人的笑声比花蜜还甜。到了国庆,玉米秆挑着饱满的棒子站成方阵,我们陪父母一包包掰下来,装三轮车运回家。父母总爱把玉米辫成串,挂满院角的木架,阳光晒得它们渐渐泛黄,春节后磨成玉米面,一部分拌进鸡食,让我每周回家都能喝上土鸡汤;另一部分喂了两头猪,一头宰了分给在县城工作的姐妹,另一头腌成腊肉,吊在灶房梁上,一年到头都飘着肉香。
平地里的水稻田,更是藏着父母的心事。如今村里有了耕地机,耕田又深又平,不用再养牛犁田;村口开着复合肥直销店,杂交水稻穗长粒满,不必再弯腰捡牛粪;农综开发项目修好了水库和水泥沟渠,清泉四季流淌,再不用连夜守在田埂引水;国家免了农业税,还发粮种补贴,公余粮的担子早卸了;收割机轰隆隆开过,镰刀、谷篮、打谷机都成了老屋角落的念想;机耕道通到田边,三轮车能直接开到稻茬田,不用再汗流浃背地背谷子。收回的稻谷从不外卖,母亲专门腾了间屋子存放,新谷压着旧谷,她说:“饱时要防饥时。”
父亲走后,我想把田地全转给村里的壮劳力,母亲却不舍。我懂,她忙碌了一辈子,土地是她的筋骨,突然歇下来,身体反倒会垮。便留了村口那小块田给她打理。每年五一,我请人插好秧苗,母亲每天天刚亮就背着小背篓去田里。她不放心,总要用手探探田水够不够,蹲在田埂上拔青蒿和杂草,顺手在埂边点上黄豆。晨光洒在她银白的头发上,汗珠亮晶晶的,脸上却写满知足。
九月中旬,稻子熟了。金黄的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风一吹,沙沙地响,混着泥土的气息,是最清润的香。母亲站在田埂上,伸手抚摸稻穗,像摸着熟睡的娃娃,嘴里念叨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和妻子选个周末,请收割机来,金灿灿的稻谷很快装了袋。接下来几天,母亲守在院子里晒谷,翻来覆去地看,直到谷粒干透,才让我周末回家扛进存放粮食的房间。看着满袋的粮食归了位,她脸上的皱纹才舒展开,露出满意的笑。这稻,这年复一年的丰收,是母亲的念想,也是我们心里最踏实的暖。
这稻花香飘了四十载,从填不饱肚子的空米缸到满屋的稻谷,从父辈的叹息到儿孙的安康。风吹过,稻浪依旧在唱,唱着土地不会辜负每滴汗水,唱着日子在穗尖上,一年比一年沉实,也唱着这越来越好的光景。
作
者
简
介
杨晓文,爱好写作。禄丰市路溪小学教师,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大山造就豪爽,小溪滋养细腻,工作之余坚持创作,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40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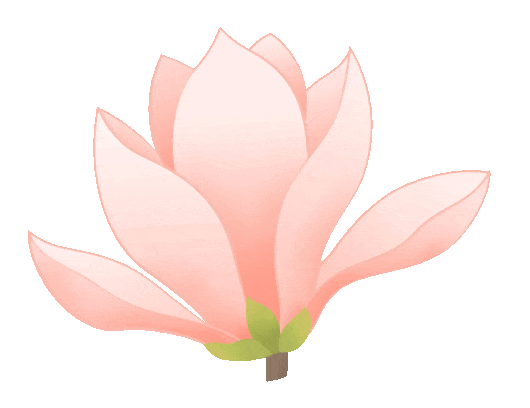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
3822183642@qq.com
文章仅用于“云南政协报”微信公众号,无稿费。
编辑:何健美
二审:张居正
终审:张莹莹
 (云南政协报)
(云南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