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苑热土|合欢花开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到高桥正是“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时候,谁都很难再遇见花。
可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越不可能遇见,就越想去试试自己的运气和缘分。
还在武定县插甸镇教书那些年,我就不止一次去高桥中学监考。我们去得迟,到高桥时已经天黑,高桥只给我一个模糊的印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常常有人把插甸和高桥连起来说:“冷插甸,恶高桥。”
插甸的冷,是出了名的,这无需隐瞒,也无需作态,可我至今没能弄明白“恶高桥”是啥意思。
越不明白,就越想去弄明白。
我们云南人把“赶街”说成“赶该”,而且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都能找到与其对应的属相街。武定管得宽的那些年,单单武定就管着鼠街、鸡街、猪街、马街、羊街、猫街和龙街;缩小了的武定,其他属相的街都走散了,只有猫街还叫猫街,龙街还叫龙街。有时候我会憨憨地问:“龙街卖龙吗?”这种小孩子的智商,我也同样用在其他十一个生肖的乡街上。猪街卖猪是肯定的,羊街卖羊是肯定的,鸡街卖鸡是肯定的,狗街卖狗也是肯定的,鼠街卖不卖老鼠,我不敢确定。可以肯定,龙街不卖龙。武定的“龙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高桥街”。
好端端的龙街,干嘛要叫“高桥街”呢?
明朝正统十年(即1445年),为了方便百姓赶集,武定军民府土知府阿宁在老街和新街之间的河面上建起了一座石拱桥。对于老街和新街的人来说,早晚吆牛牵马从桥上过,这座桥给人一种颤巍巍的感觉;对于喜欢拿鱼摸虾的人来说,在桥洞下摸泥鳅、拿石蚌、钓鲫鱼、捞米虾、避风雨,这座桥给人一种巍峨的感觉;而对于跟随父母来赶老街和新街的孩子来说,这座桥真的很高,不敢独自走上去。
老街和新街,原本是两座灰头土脸的村庄:石板铺盖的土掌房,光腚露臀的孩子,脚后跟开裂的男人和女人,趴在村口吐舌头的土狗,炊烟中母亲唤儿吃饭的声音……这一切,都有。依山傍水,居住的人多了,经商的人多了,有人就开起了店铺,做起了买卖,两个村子渐渐形成了街子,有了街子的模样。明里不作声,人们暗里却使劲,都希望自己的街越来越大,别人的街越来越小——老街买来新街卖,新街买来老街卖,比谁的生意更好,比谁赚的钱更多,比谁的房子更漂亮。渐渐的,不相上下的老街和新街,就以中间这座桥为名,统称为“高桥街”了。
如果想要追根溯源,这个“街”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足见商朝的商业已经很发达,足见商朝的官方已经十分重视商业,也足见商朝的文人墨客已经参与商业活动了。殷者,丰盛也;商朝迁都于殷,故商朝又称殷商。殷商殷商,善商则更加殷实,人民更加富足,因此商朝成为中国寿命最长的朝代之一。“街”是一个形声字,从“行”,“圭”声,一看就像人捧着斗升在集市漫步做生意的样子,怎么看,都像咱高桥人。
“街”字,本义是指较为通达的道路,特指城邑中宽阔的道路,后来转指集市贸易的地方。高桥龙街,恰好已然具备了这些条件。高桥街,是108国道自西向东穿过的乡街,既是国道,又是街子,这种特殊待遇,就连做了母城的武定,也还差着一截呢。
武定高桥人,就像浙江温州人一样,生意细胞特别发达,经商意识特别强。虽然距县城四十余公里,可在武定县城开菌子火锅店的,都是高桥人;他们把菌子火锅店开到武定,开到楚雄,开到昆明,开到更远更大的城市里去,赚回更多的钱。在高桥人眼里,男人手里不捏着几桩顺手生意,很难立足。在他们看来,经商赚钱才是最快乐的:即使有了一份细水长流的工作,他们也不会放弃做点生意;即使拿着很多的退休金,他们也依然经营着自己的门店;即使“窝”在村里,他们也或大或小经营着一桩买卖。就是在村里搞种植业和养殖业,他们也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同植同养——过剩的时候卖不出去,稀缺的时候没有卖的。就拿种植茭白来说,他们这块田比那块田迟种三五天、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这样就可以交错着种,交错着采,交错着卖,既有劳力,又有市场。看见别人的旅店生意红火,他们不会一窝蜂去开旅店,而是在旅店旁边开起百货店,在百货店旁边开起饭庄,在饭庄旁边开起早点铺,在早点铺旁边开起茶室,在茶室旁边开起茶叶铺……即使在土地上搞种植业和养殖业,他们也绝不雷同:你家种荞麦,我家种玉米;你家种洋芋,我家种芋头;你家养牛,我家养羊;你家养猪,我家养鸡……店店有生意,家家有钱赚,人人有饭吃。高桥人的经商意识,似乎是与生俱来。从高桥出来的人,都有很高的经商智商:即使是家家都有的麦面,他们也能从中找到商机,做出名气很大的高桥大粑粑,卖到县城,卖到州城,卖到省城;即使是一碗凉粉、一碗米线,高桥人做出来就是好吃,让人不嫌路远,跑到高桥来吃凉粉、凉米线;一朵松茸在十个高桥人手里转了一圈,十个高桥人都赚到了钱。外地人要想到高桥当上门女婿,生意上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若要富,先修路。”这是闭塞农村的呐喊。在武定高桥,这句话真正实现了它呐喊的意义。沿着108国道搞产业,这是高桥的特点,也是高桥的优势。赊甸村的蓝莓,花桥村的草莓,岩子村的青豌豆和莲藕,海子村的茭白……一路一带,全都摆放在这条国道两侧,方便种植,方便采收,方便收购,方便运输。在勤劳的高桥人手里,土地一点不浪费,一寸不荒废:草莓刚一摘完,塑料温棚里就长出了饱满的豆荚和带着黑须的甜脆玉米。
没想到,“人间四月芳菲尽”的高桥,正是合欢花开的时候。从老滔到花桥,从花桥到海子,从海子到马鞍山,从马鞍山到沙拉箐……合欢树都像长了手、长了脚,我走到哪里,它们就跟着走到哪里。在村子旁边,在田野旁边,在河水旁边,在水井旁边……或几棵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开出繁硕的花朵;或只一棵,却有伞盖一般笼起巨大的树冠,顶上的花朵成千上万。毛茸茸的花朵,粉嘟嘟的颜色,远看像伞兵天降,近观像执扇舞女,托举着粉红色的舞扇在我面前翩跹起舞。
这倒不是因为五月的高桥无花可看。就是不开花,合欢树也极其好看:它高大的身躯配上微微光滑的树干,葳蕤的树枝配上成双成对的叶柄,微微下弯的叶柄上配上米粒大小的叶片,本就是一种好看。它那么高大,却有着含羞草那般纤细的叶柄和娇小的叶片,而且叶柄和叶片都是成双成对——它们白天分开,到了夜晚就像夫妻一样自然合在一起,因此合欢树也叫“夜合树”。合欢花,像舞女手里的舞扇,又像年少时贪玩的烟花,柔软的花针从下往上、从集中到分散,就像火药喷射的火苗,晶莹剔透,给人一种欢天喜地的感觉。
在高桥,这样的欢天喜地,一直跟着我走进了沙拉箐。
高桥,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也是武定唯一有老红军的乡镇。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和方向走,到了马鞍山,地势陡然升高,地形地貌陡然大变。可以说,“马鞍山”是高桥镇的分水岭:2006年撤乡并镇,原石腊它苗族乡连人带地并入高桥镇,花山节就成为高桥镇每年必办的传统节日。这条分水岭往东往南,是高桥镇的鱼米之乡,地势低平,交通便捷,土地肥沃,适合种植水稻、油菜、蚕豆、小麦、茭白、草莓,发展水产养殖业,依托108国道,高桥人开办起各具特色的农家乐;这条分水岭往西往北,是高桥镇的山区,地势高寒,交通受限,经济滞后,主要种植玉米、小麦、洋芋和烟草,发展山区畜牧业。越往山里走,民族融合就越加凸显,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往往由不同的民族共同组成,特别是到了“弯腰树”一带,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就越加显著。
“合”是一个字,又是三个字——无论是“人”、“一”,还是“口”,都特别简单,牙牙学语的小孩张口就会说,而“人人有口饭吃”的意思也一看就懂。合欢是装修豪华居所的必备木料,是炎热五月里欢天喜地的绒花,是治愈人类痼疾的良药。
趁我在高桥眯一会儿的工夫,热乎乎的五月就越来越成熟了。不远处,端午节和各民族共同合欢的花山节,正朝着高桥和我,越走越近。
作
者
简
介
王胜华,苗族,云南武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散文主要发表于《民族文学》《散文选刊》《海外文摘》《文艺报》《云南日报》《金沙江文艺》等。多篇散文选入全国多省、市、自治区中学语文试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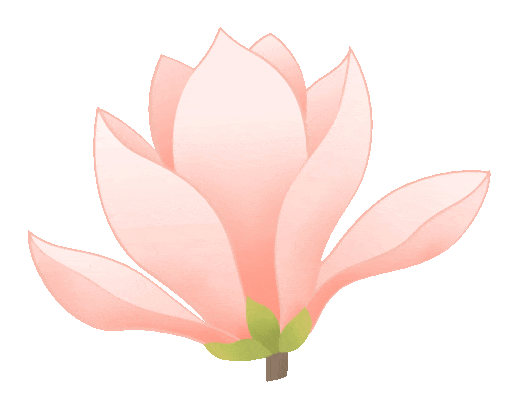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
3822183642@qq.com
文章仅用于“云南政协报”微信公众号,无稿费。
编辑:何健美
二审:张居正
终审:张莹莹
 (云南政协报)
(云南政协报)


